苗家人借助锉花表现理想的追求
如果说,人们借助民间艺术美化自己那种有缺陷的生活,多少包含着一种对困境的自我解脱的话,那么,苗族锉花对生活的理想追求则更为积极。它充分肯定现实生活中的美,在对现实生活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它们的否定和扬弃,包含着对它们的改造和建设,寄希望于应有和会有的未来。
理想是现实的美好延伸,是未来的合乎人愿的发展趋势,因而它依然是对观念的一种补偿。在这种补偿中,人们企求的已不是对暗淡生活的增彩和染色,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感官满足,而是要把现实生活的今天推向它的明天和后天。凭借艺术的翱翔,在今天梦一般地去观照和眺望美好的明天,从而在视觉世界中展现今天想实现而无法实现的东西。这些理想,由苗族锉花这一民间艺术表现出来,便是其中所祝颂、所肯定、所给予审美观照的吉祥如意一类事物及其价值属性。概括而言,苗族妇女在锉花艺术中表现的生活理想主要是“福”、“禄”、“寿”、“喜”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与这四个方面的艺术题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造型和图案,在苗族其他手工艺制品如蜡染、雕刻中也屡见不鲜。
“福”的方面包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家庭祥和、生计宽裕、事业发达、功成名就、夫贵妻荣、子孙繁昌、宗族兴隆等等。它们在传统文化中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基本要素,也是黎民百姓最古老、最经常也是最喜欢做的梦。福不止一,民间素有五福之谓。《书经》云:“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这样看来,则见福为吉祥之首,内包了禄、寿、喜的某些因素。因此,求福、求双福、求五福乃至拜万福,当然地体现了平民对自己的生活在自然和社会方面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最大肯定。“福”见诸民间艺术的题材和表现形式是极为丰富的,诸如“福禄喜庆”、“迎祥纳福”、“五福同庆”、“三阳开泰”、“四季花开”、“太平景象”、“新韶如意”、“福增贵子”、“华封三祝”、“天官赐福”、“竹报平安”、“和合如意”、“富贵荣华”、“吉庆有余”、“连年有余”、“一多十余”、“安居乐业”、“福寿双全”、“福禄双全”以及单一的“福”字造型等。苗族锉花中常以蝴蝶、鲤鱼、蝙蝠、肥猪、羊等动物组成象征幸福的图案。若从现实的根源来说,对于“福”的这些描绘与希求,恐怕正是黎民生活太缺少幸福的缘故。幸福的呐喊正是对不幸现实生活的反观与抗争。
“禄”本来是晋升、利禄的意思。《论语》云:“人有命有禄,命者,富贵贫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可是,在乡民那儿,“禄”转换成为财与富的经济因素或发财致富的机运了。经济富裕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与保障,对于长期贫困的平民百姓,想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以增加财富,自然是十分迫切的事。苗族和汉族一样,他们也追求着财富象征的“禄”,在民间艺术里以多种方式巧妙地表现着自己对“禄”的渴望,既显示了经济的饥饿与欲求,又不失重义轻利的传统和体面。苗族锉花中,求禄宗旨下展开的艺术题材或创造的艺术形象主要有这样一些:“双鹿图”、“连年有鱼(余)”、“金钱蝴蝶”、“聚宝盆”、“金银山”、“摇钱树”、“财神”等等。这些传统图案,并不表明人民大众是一些利欲熏心的金钱奴隶。恰恰相反,因为他们经常受到缺吃少穿无钱花的种种威胁,受到有钱人的挤压与作弄。这种惨境引起了他们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聚宝盆”、“摇钱树”一类艺术形象,去松弛自己对财富的苦恼与焦虑,借以鼓起生活的勇气。
“寿”是“福”的延伸和进一步具体化,中国人素来是看重生命的久长乃至永存的。长寿历来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书经》中的“寿”为“五福”之首。《诗·小雅·鸳鸯》云:“君子万年,福禄宜之”,把长寿福禄作为得道君子的佳境。《蔡传》则云:“人有寿,而后能享诸福。”意味有命才能谈福。逢生庆寿,久为民俗传统。《诗经·豳风·七月》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歌咏。《史记·封禅书》“寿星祠”云:“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也。”祈福寿的古俗已进入了神话境界。元方回《桐江续集》二十《戊戌生日》诗:“客舍逢生日,邻家送寿星。”亦可见邻里贺寿之古俗。苗族民间,通常六十岁起始做寿,亲友多以酒肉糖面作寿礼相送。子孙则设寿堂拜祝,富户人家尤为铺张。在这些古风传扬中,苗族逐渐形成并不断传承着一些关于做寿、贺寿的民俗事象。俗谚云:“家有一老,好比一宝”,“生日一到,儿女尽孝”。人们希望劳禄一生到头,要有一个好的晚年。于是企求健康长寿,多看几天世界,多过几天好日子,便成为福禄之后的又一大生活理想。人们一怕身体不好,有福不能享;二怕老来贫寒,身后凄凉;三怕家人不健,半生早逝,有所谓“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是人生“三大不幸”的口头禅。民间谚语常说:“无病便是福”,“眼康脚健是大福”,“六十岁有福才是福”,“禾怕老来虫,人怕老来病”。这大概是因为年老体衰,得病难愈,或者年老丧失劳动力,得病更遭人弃的缘故。因此,人们常把人的健康长寿,把夫妻的白头偕老这类因素构成的“寿”,当作非常重要的生活价值在民间艺术中加以肯定。苗族民间艺术的“寿”主题及其各种具体造像,也就因为“寿”的种种民俗行为、语言与心理得到形成和发展,派上了为庆寿、祝寿一类的古风古俗铺张添彩的用场。这类作品极为丰富,最常见的有:“福鹿”、“寿星”、“三星”、“百寿”、“五福捧寿”、“麻姑献寿”、“耄耋富贵”、“鹤寿延年”、“鹤寿松龄”、“福寿双全”、“鹿鹤同春”、“福贵寿考”、“鹤献蟠桃”等等。“寿”在苗族锉花中还抽象变成![]() 和
和![]() 的连续图案组成各种花边,也有的为单独纹样,在锉花中成为中心图案点。它们都生动地表达了民众祈寿延年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理想,同时,它们也是锉花艺术中永唱不绝的生命礼赞的重要乐章。
的连续图案组成各种花边,也有的为单独纹样,在锉花中成为中心图案点。它们都生动地表达了民众祈寿延年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理想,同时,它们也是锉花艺术中永唱不绝的生命礼赞的重要乐章。
“喜”,是生活幸福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是指生活诸事遂心如意,充满着乐融融、喜洋洋的良好气氛,更重要的是指能够给生活带来幸福快乐的各种境遇和事件。民间俗语中,“喜”的系数最多不过“四”,“四喜临门”为喜事之最。民间传说的“四喜”,一为久旱逢甘露;二为他乡遇故知;三为洞房花烛夜;四为金榜题名时。汉族有“四喜人”的剪纸图像,就是象征着这四件事。如果把这四件喜事推开而论,那么,它们则是如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十分困难的时期碰上了使困难得以解决的机遇和条件,使人们愁容顿解,或得到了意外收获,让人喜出望外;二是人际关系、社会交往中偶然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件,造成了情感上巨大的波澜和愉悦;三是久久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事业有成,意味着人生的急剧改善与提升;四是婚姻的圆满,各种佳期降临,让人沉浸于幸福的喜悦之中。这些事件,在苗族民间艺术创作中,大抵用这样一些题材和造型作了描绘:“喜”字、“春牛”、“五谷丰登”、“喜上眉梢”、“喜鹊闹梅”、“喜从天降”、“鱼樵喜乐”、“鸳鸯戏荷”、“凤戏牡丹”、“龙凤呈祥”、“龙飞凤舞”、“和合二仙”、“鲤鱼跳龙门”、“连年有余”等等。它们无一不艺术地、形象地展示了旧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所期盼的那些寄托着自己希冀的各种幸事、好事、美事、乐事。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生动的事例,那些穷乡僻壤的生活困难者新婚,尽管房屋老旧,家具简陋,但也要把火红“喜”字、喜花、喜联以及其他各种美好的祝颂剪出来,画上去,糊到黑黄的土墙上,给破旧的生活场景添加一层新欣的气象,进而给当事者凑一分热闹,增一分喜气,鼓一分信心。自然,这类文化行为是对未来的美好前景的一种设计和一种艺术的演示。
综观以上各种吉祥寓意图案和装饰纹样,首先,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大都是以比喻、双关、拟人、谐音等表现手法,组成一系列具有一定吉利意蕴的图像。它们历史悠久,已形成固定的模式,达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其表达方式,不外是名称谐音表达、图案形象表示、附加文字说明等。它们之所以成为现实生活的一种精神补偿,首先在于它们颂扬和美化的事件,的确是一些幸福吉祥、令人惬意的事件。比喻新春之喜,即使一年平淡无奇,而一年伊始,万象更新,人们也总要热闹一番,家家户户写春联、贴门神、挂门笺以渲染一派喜气,盼望着来年的吉运。其次,这些吉祥图案的艺术创作,也多用于喜庆的时间和场面。对于吉祥,《庄子·人间世》云:“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唐成玄英《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前人说得很清楚,“吉祥”不仅是对福善之事的称赞,而且是嘉庆活动的表征。所以,从它们的内容到形式乃至时空场合,都是令人舒畅、愉快的事情。当黎民大众把这平时少见的福善之事与嘉庆之举,以艺术的形式记载和描绘出来,并装点在平平凡凡的生活空间、建筑、用器、饰物、服装、贺礼之中时,它们便在福事庆举过后,依然留存在生活里。进而,它们也必然把福事的气息与喜悦,把嘉庆的盛况与欢乐同样留存在人们心里,时常引起人们的美好回忆。这样,虽然平常的日子过得相当苦涩,但人民对于现实的窘境终于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的出路。人们在自己创造的艺术世界里看到了光明与前景,从而也就实现了对现实生活加以理想改造和加以美化修饰的目的,还获得了一种美化与补偿现实生活的文化平衡效应。第三,苗族锉花艺术除了因它们的内容是生活的理想化、美化而具有补偿作用外,还因为它们在被运用于对民间福善之事进行嘉庆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功用与意义:祝贺与祈求、纪念与期盼。若从功用看,则它们半是对创伤的抚慰,半是对幸福的追求。若从时间方位来讲,则它们半是对历史的肯定,半是对未来的向往。若从空间方位来看,则半是对他人的祝贺,半是对自己的鼓舞。在忘情的皆大欢喜中,道贺者总是藏着一份不忘情的窃窃私喜。正像一幅“五福捧寿”的锉花作品,对于寿诞老人,既庆贺那福寿有年的历史,更追求那“贵寿无极”的未来;对于锉制这一作品或馈赠这一礼物的他人,则在庆祝主人这一福寿的同时,暗含着自己的观照与比附:也将“如此贵寿”乃至“无极”。诸如此类,里面隐匿有深层的文化密码与艺术用心。惟其如此,苗族锉花对于现实生活的补偿功能,才能在这一艺术的创作和观赏的主体那儿得到发挥和实现。
表现“喜”的锉花3幅
日期:200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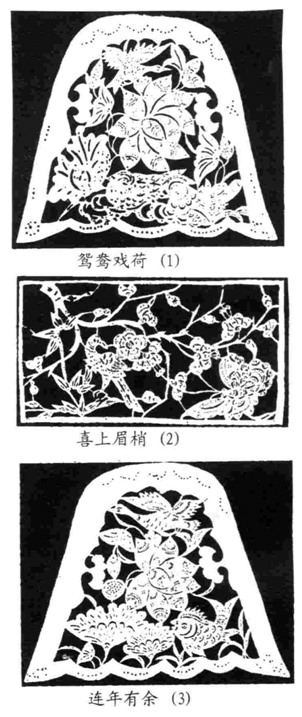
 关闭
关闭  打印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