锉花纹样之鸟纹样
鸟纹样出现在锉花中的频率较高,几乎所有造型纹样中都可发现鸟的身影。这些众多的鸟可分为写实的鸟和写意的鸟两大类。从名称上看,也有具体的鸟和不具名的雀两大类。
写实的鸟主要有前述的凤凰最为多见,其次较多见的是鹤、鸳鸯、喜鹊、燕子、鹭鸶、鹌鹑、孔雀等。写意的鸟主要是和各种花草果实组合而成的不具名的雀,属组合花鸟或组合果鸟,在造型和构图上,与写实类的鸟均有不同。
鹤一向被视为羽族之长,称之为“一品鸟”。汉族以鹤构成的吉祥图案,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有时喻贤能之士,有时喻父子之道,在民间更多的是象征长寿。如“一品当朝”、“一品高升”就是画鹤立于潮头或翔于云间,还有“指日高升”为日出时仙鹤飞翔的图案。其他如“松鹤同寿”、“龟鹤延年”、“鹿鹤同春”等图案更是屡见不鲜。《相鹤经》云:“鹤者,阳鸟也,而游于阳。因金气、依火精以自养,金数九,火数七,故七年小变,十三年大变,百六十年变止,千六百年形定。体尚洁,故其道色白;声闻天,故其头赤;食于水,故其喙长;轩于前,故后指短;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凋;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大喉以吐,故修颈以纳新。”总之,堪比才俊,俨然君子。这些都是鹤被视为一品鸟的原因。在汉族传统鸟纹样中,鹤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仅次于凤。明清官服的补子纹样中,文官一品均为仙鹤。民间观念中,鹤与龟同为长寿之王,故常以龟寿、鹤寿、鹤龄为颂人长寿吉语。鹤还常与松树组合成各式松鹤图,见于画稿、文具、衣料、器用之中,床上用品尤为多见,鹤还与道家相关。传统鹤有仙风道骨,常作为仙人骑乘,在“寿星献寿”和“群仙献寿”图案中,南极仙翁与八仙均骑于鹤背在空中飞翔,所以民间挽联中也多见鹤的词章,如乘鹤跨西、驾鹤归仙、鹤驾西天等。
鸳鸯作为夫妻和谐美好、忠贞不渝的象征,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人们歆羡鸳鸯的双飞双栖、恩爱无间,故将夫妇之情、爱情之义参寄寓其身。关于鸳鸯的特性,古来记述颇多,古人称之为“匹鸟”。崔豹《古今注》云:“鸳鸯,水鸟,凫类。雌雄未曾相离,人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鸟。”民间传说鸳鸯形影不离,左雄右雌,飞则同振翅,游则同戏水,栖则连翼交颈而眠。如若丧偶,存者终身不匹。这种特性与传统五伦中的夫妇之义恰合,所以也就引申成为爱情、婚姻美满的象征。锉花中的鸳鸯多用于荷包、鞋垫等爱情信物的图案中,常与荷花相组合。另外在高腰围裙的裙头花和被面、门帘中也较常见,其造型风格均以阴刻为主,特色上与汉族鸳鸯一致,属“引进品种”。
喜鹊在民间认为是一种吉祥鸟,具有感应预兆的神异本领。《苗族古歌》“跋山涉水”章节中说,苗族西迁到今黔东南地区以后,喜鹊报信说,这里盛产稻米和棉花,是安家的好地方,人们才定居下来。人们请喜鹊在寨边枫树上筑巢安家,比邻而居,朝夕相望。苗族谚语云:“喜鹊叫,客人到。”这种观念与汉族的一致。如《西京杂记》引陆贾的话:“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这里就预示客人的到来。另外,喜鹊叫也预示喜事到来,王仁裕《天宝遗事·灵鹊报喜》云:“时人之家,闻鹊声,皆曰喜兆,故谓灵鹊报喜。”又《宋书》载,徐羡官拜司空时,有两只喜鹊在太极殿的飞檐上鸣叫。民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每年七夕相会时,都是喜鹊搭桥使之渡河相会。《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后世遂将沟通男女婚姻之事为搭鹊桥。苗族锉花中的喜鹊多与梅花构成“喜上眉梢”图案,除此之外还有喜相逢、喜在眼前、喜报三元等图案。
燕为小飞鸟,其形象俊俏,飞舞轻盈,尾剪春风,与人友善,很早就为人所喜爱。久而久之,燕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吉祥物,象征春光,比拟情侣。古时称燕为玄鸟,《诗经》载,商的祖先是其母简狄吞食燕卵而生,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燕既有这样的名称、出生及神话,后世便视其为祥瑞灵物。燕巢于檐间或集于殿阁,被认为是主家友善、家道发达的征兆。苗族非常喜欢燕子,在《苗族古歌》“跋山涉水”章节中,说是燕子带头引路,人们才找到好地方定居下来。苗族以燕来筑巢为吉兆,严禁伤害燕子。不仅让燕子在居室外筑巢,而且还让燕子在居室内筑巢,还特意在巢下钉一块木板以保护燕巢。锉花中的燕多为侧面造型,突出双翅与剪刀状的尾巴,多表现在衣边花和围裙花样中,常与牡丹、菊花等折枝花卉共同组成“春回大地”、“春来花开”等图案。一般为单燕,较少双燕。
鹭鸶、鹌鹑、孔雀在苗族锉花中,也常作为鸟的纹样与荷花、竹子、牡丹等花卉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鹭鸶采莲”、“安居乐业”、“花开富贵”等吉祥图案。此三种鸟都作为清代的文官服中的补子图案,鹭鸶用于六品,鹌鹑用于八品,孔雀用于三品。看来,这些鸟雀之间还是有地位差异的,这些差异当然是人为因素所致。古人称孔雀有九德,为文明之鸟。(逸周书·常训)谓九德为“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可谓大仁大德。鹌鹑就很不起眼了,位列九品中倒数第二,它的特点是居不择地,随地而安,故“鹑居”指居无定所。汉族俗语中还有“秃尾巴鹌鹑”一说,引申为破衣褴衫,形容不佳,故有鹑衣、鹑衣百结之说。杜甫诗有“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骆宾王诗有“鹑服常悲碎,蜗庐未卜安”之句。汉族民间谚语还说“鹌鹑、戏子、猴,不可交朋友”。鹌鹑几乎无一可取,好在它与“安”谐音,所以也就挤进吉祥鸟的队伍中来了。
以上是写实的鸟的表现及特征。写意的鸟在锉花中是些无名无姓的小型鸟,故称之为雀,它的外形比鸟小,一般与花卉组合成装饰图案,多用于服饰的衣袖边、裤脚边、前襟边等边角的装饰中。除了侧面造型之外,还有不少正面造型。正面造型突出雀的头部和尾巴,另外加两只翅膀,几乎没有躯体。双翅的位置也常常根据图案需要,自由灵活处理,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翅膀有时长在脑袋上边,有时长在肚子下边;有时翅膀长到树枝上去了等等。但却具有一种新颖别致的审美效果。这类纹样中,有时还以花果或花草树叶构成鸟身鸟形,或鸟的双翅、尾巴变成了花枝花叶,鸟的躯干变成了一朵花或变成石榴、变成桃子、佛手等。从造型上看,均表现为极为复杂多变的花鸟组合纹样。(见附图)

花鸟组合花边样
(1)鸟身与石榴、花卉组合合一
(2)鸟身与菊花、桃组合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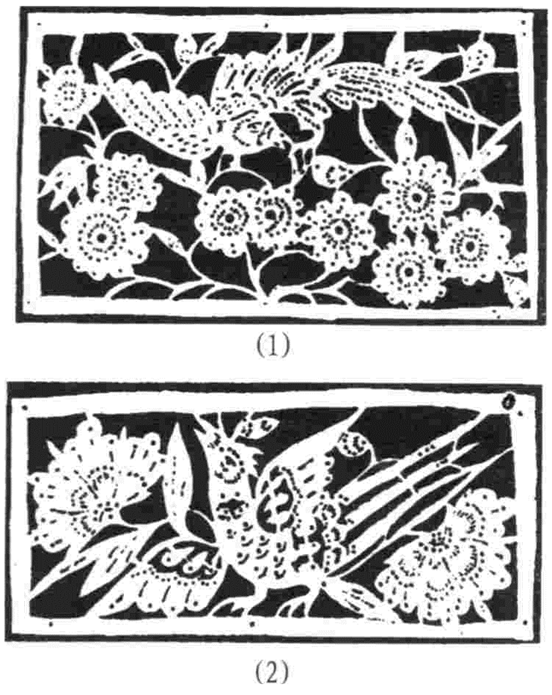
花鸟组合
苗族青年学者杨正文先生指出,苗族存在鸟崇拜,具有丰富的鸟文化。鸟纹在苗族服饰中的表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湘西方言区,二是川黔滇方言区,三是黔东南方言区。每一区的鸟纹都有其发育成型的代表,第一种类型以湘西凤凰、花垣、贵州松桃为代表。(杨正文著:《苗族服饰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这里要补充的是,此类型的鸟纹还应加上泸溪、吉首两县市。杨正文指出,汉文献记载的上古神话传说中有关于鸟崇拜和鸟文化的描绘,它与苗族先民神话传说中的鸟崇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或文化传承关系。《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云:“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郭璞注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神异记·西荒经》云:“西方荒中……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这个三苗国,就是今苗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对此,专论已不少,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胳下有翼”几个字,可以理解为祭祀中的特异造型,也可以理解为后来所谓的“卉服鸟章”。与三苗国同姓的被研究者们认为是苗族先民建立的“欢头国”(欢头、![]() 兜相通)也是一个崇尚鸟纹的上古国家。《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曰:“欢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曰欢朱国。”同书《大荒南经》又载曰:“大荒之中有人,名曰
兜相通)也是一个崇尚鸟纹的上古国家。《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曰:“欢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曰欢朱国。”同书《大荒南经》又载曰:“大荒之中有人,名曰![]() 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神异经·南荒经》记载:“南方有人,人面鸟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有翼不足而飞。一名
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神异经·南荒经》记载:“南方有人,人面鸟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有翼不足而飞。一名![]() 兜。《书》曰:‘放
兜。《书》曰:‘放![]() 兜与崇山。’一名
兜与崇山。’一名![]() 兜。”对于欢头与三苗之间的关系,《山海经·大荒北经》载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
兜。”对于欢头与三苗之间的关系,《山海经·大荒北经》载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 头,
头,![]() 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由此可结论说,三苗与
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由此可结论说,三苗与![]() 头都是居住在南方的同姓的民族,而且是崇拜鸟或以鸟作为图腾的民族。由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今天的苗族构成中,有一支或数支苗族的先民在远古时代把鸟作为图腾,因而才有今天丰富的鸟纹饰造型。
头都是居住在南方的同姓的民族,而且是崇拜鸟或以鸟作为图腾的民族。由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今天的苗族构成中,有一支或数支苗族的先民在远古时代把鸟作为图腾,因而才有今天丰富的鸟纹饰造型。
苗族青年学者杨![]() 国先生通过对苗族服饰中的鸟纹分析研究后指出,鸟作为一种雄性生殖器的象征,鸟具有生殖的意象,是生殖崇拜的一种反映。苗族服饰图案中的姬宇鸟、锦鸡、羽人像等等,是鸟图腾、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一种综合反映,它体现了苗家人对自己先祖姜央、蚩尤、欢兜以及蝴蝶妈妈的永恒纪念与缅怀。(杨鹃国著:《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国先生通过对苗族服饰中的鸟纹分析研究后指出,鸟作为一种雄性生殖器的象征,鸟具有生殖的意象,是生殖崇拜的一种反映。苗族服饰图案中的姬宇鸟、锦鸡、羽人像等等,是鸟图腾、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一种综合反映,它体现了苗家人对自己先祖姜央、蚩尤、欢兜以及蝴蝶妈妈的永恒纪念与缅怀。(杨鹃国著:《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就苗族锉花中的鸟纹而言,由于经过不同时代的演变以及与汉族鸟纹的交往与“迁徙”,在造型方面它可能保持了一些古朴原始的原创意味,但是有关它的象征意义则几乎荡然无存了。在调查中,我采访了众多的锉花能手,问他们为什么都喜欢花鸟,他们几乎都说“花鸟好看”。这可以理解为美的创作动因在起作用,有一种追求美和创造美的自觉意识和本能在支配着他们。因此,对花鸟纹样的选择与表现也就成为正常之事,是一种对美的追求与表现。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花鸟写意变形图案,那就是创作主体在创作灵感激发下的神来之笔,是进入到艺术的无我境界中的自由创造的产物。
日期:2001-12


 关闭
关闭  打印
打印